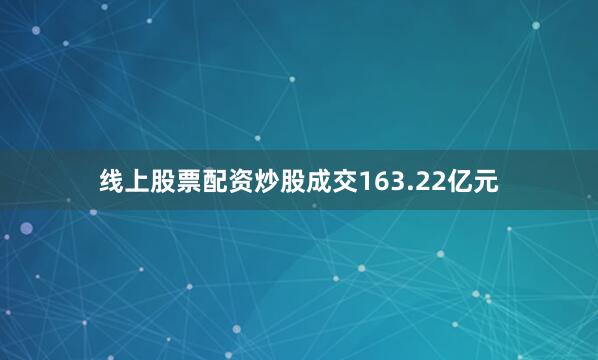李新月把影像当成日记来书写,亲情爱情友情工作,迷茫与未知全盘托出,疼痛与成长毫不避讳。“新月”是影片的题目,也是导演的名字——这是母亲起的,来自于她在生产过程中的疼痛和混乱中仰望的美好。引领着导演回望她所出生的九十年代,也与母亲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着新的连接。
2020年24岁的李新月,结束北漂生活,回到了离开六年的老家哈尔滨。
人生的轨道在24岁按下刹车键,她开始诚实地回望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北漂人生,以及当下上岸备考的重重关卡,同时思考着这部“自传”要走向何方。
“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片当时的片子要往哪走,但是我觉得生活需要一种动态的感觉,就是生活需要动起来。”这不是一部开始就想好了怎么拍的纪录片,甚至创作的过程几度卡壳不知如何走下去,这时就显示出了团队的重要性。
李新月分享了她如何在草场地工作坊伙伴们的助力下,通过阅读-写作-剪辑等步骤反复多次讨论,集体共创完成了这部作品。这不仅关乎创作,更是一种高密度社群方式,也促使新月的人生发生了重大改变。
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只要我们还在看着同一轮新月,还在共享着同一个时代记忆,就能在这部片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注脚。
《新月一章》入围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,这对新月是一次巨大的鼓励。她已经开始了《新月二章》的创作,回到姥爷村里,修旧屋,包一亩稻地,一边种地一边拍片,一边生活。“种地是最诚实的劳动”,她的生活与创作,都开始了新的篇章。
以下是凹凸镜DOC专访《新月一章》导演李新月:

《新月一章》:在疼痛和混乱中仰望的美好
采访撰文:冯琛琦
编辑:张先声
凹凸镜DOC:片名《新月一章》由来是什么呢?
李新月:这片子来自草场地工作站线上的一个工作坊,叫“影像/写作工作坊”,这个工作坊没有门槛,对所有人都开放的。参加工作坊之后,我想要在片子里梳理一下自己,但是对于创作没有什么概念。后来就开始写到我是回到哈尔滨之后,跟我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问她我的名字(新月)由来,我之前以为是这个名字是就是“新年的月亮”而已。
原来,在生我的那一天,妈妈躺在床上生的很痛苦时,看到了窗外有一轮新月升起来。刚开始我爷爷给我起过李娜、李娇、李婷这种的名字,妈妈觉得太土了,我姥爷又起了一个叫李双莹,意思是就是室中藏宝。我妈又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小气,最后就想到了这个新月。
我在工作坊写到了这个,大家反馈说这个名字,可以是一个人的名字,但也是一种寓意——在疼痛和混乱中仰望的美好凝固到了我的名字里。是在残酷的现实里面,母亲对我的一种美好的期望。另外就是吴文光老师延伸的,最早有一个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叫“新月沃土”,民国时候有一个新月派,徐志摩等人组建的文学式的写作等等。“新月”就变成了意象。
“一章”是系列创作的一个编号,新月一章二章三章这么这么往下,因为这也涉及在草场地(工作站),个人创作的一种方法论,大家不只是做一部片子。比如说早期“村民影像计划”中的邵阿姨(邵玉珍),她就是拍村民有关的内容,片名就是《我的村子2005》《我的村子2006》《我的村子2007》这样一年一部的方式,像章梦奇就是自画像:47公里系列。我理解是在一步步实践,可能不成熟,但每一年是在往前迈步的。所以当时就是加了这个“一章”,期望就是二章三章往下拍下去。

片中与父母婚礼录像带投影表演,或是其他
凹凸镜DOC:片中大量使用了90年代的录像,包括你没有出生之前的父母婚礼。他们也是特别爱记录的吗?这些老素材你是怎么收集到的?
李新月:那个时代有一股下海潮,我父亲从工厂里面出来,靠摆台球摊弄游戏厅,赚了一些钱,他花钱在婚礼的时候找一个摄像师把婚礼过程拍下来,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再看了。等我回哈尔滨之后,想到创作这件事情,才想到可以拿出来看看。
我妈属于比较敏感细腻型的,包括她写的日记。其实我做这个片子的三年时间里,她已经做了三个片子了。2021年的时候,草场地工作站的伙伴们发起的“母亲影展”,鼓励妈妈们拍自己的生活,我妈拍了三部纪录片。
比如在我的片子里,你可以看到我和她生活在一个很蜗居的地方,房间还有渗水的情况,那是我的视角,但是她的视角里看,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,这个空间怎么去装饰它,她如何在其中去享受这种孤独。

新月父母的婚庆录像带
凹凸镜DOC:能看出来片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不同样式的画面表达,比如开头的手绘新月、在线地图录屏、桌面电影、投影、旧影像资料等,这些不同类型的画面是如何编排的?
李新月:是在创作过程中实验出来的,像写作一样去做影像。我想把名字的由来放在最开始,但是我什么素材都没有,那怎么办?那就开始实验,比如之前尝试过我和我妈面对面坐着,她给我讲我名字是怎么来的,但是那个效果不是很好,讲的比较细碎且失去了凝练的寓意。
后来吴文光老师帮我找了一个专业的人来画,但是又感觉那不是我的东西了。之后我自己也试过黑纸白笔,但又没有铅笔那种手绘一笔一划的感觉。所以最后就是实验出来用这种方式。

草场地工作坊中实验“画新月”
包括你提到的地图那部分,在工作坊过程中,梦奇分享了一个叫“桌面电影”的创作方式,我在 B 站上能看到Kevin B.Lee的短片作品,就在一个电脑屏幕上,可以实践出各种东西又是打便签,又是打字,又是打视频。我就想到我的片子北漂这部分,就可以用“桌面电影”行驶呈现,它像一个抽屉一样,可以把日记、照片、地图……任何方式就在这个桌面里面完成。
凹凸镜DOC:片子中没有配乐,关于声音/音乐的处理是怎么考虑的?以及拍摄器材是什么,设备的选取是否影响你的创作?
李新月:音乐是完全没有考虑,因为影像本身已经感觉已经足够了,就没有想过音乐。
片子是我一个人拍,一个人剪辑的。设备的话是一部摄像机,我用自动挡,这经常会被工作坊的小伙伴们吐槽。因为是在家里拍的比较多,可能一次拍个两三个小时,大量的是无目的的拍摄,重点还是在剪辑的时候重新去阅读素材。
片尾跑步的那个素材是手机拍的,来自于真实生活。有一段时间,我几乎每天都在松花江边跑步。当时正好(草场地工作站)有一个“阅读素材工作坊”,大家每个人分享六分钟左右的一个不剪辑的素材。
当时,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片当时的片子要往哪走,但是我觉得生活需要一种动态的感觉,生活需要动起来。正好那时候我在跑步,那就拍一个在跑步的素材吧,拿手机边跑边拍,当时没想过要怎么用到片子里。
在剪辑阶段,觉得跑步是一个很合适的意象——做完这个片子,对自己整个26年人生有了回溯之后,这个人依然不知道要去哪里,但是他是在一个动态的情境下往前走,可能是一种寓意。

从新月妈妈的家望向窗外
凹凸镜DOC:全片诚实地面对自己,像写日记一样,在如此开诚布公剖析自己和家庭的过往时,什么对你而言是最难的?
李新月:是在剪辑的时候,因为如果就靠我一个人,我是剪不出来这个片子的。
在我回哈尔滨没有工作很混乱的那段时间,我决定梳理一下素材,这些素材很多是杂乱无章的,拍了不知道要怎么用,最开始剪出了一个3个小时的版本,都是堆砌的不成立。但后来在草场地工作坊,像吴老师还有梦奇,还有一个伙伴哈比,我们一起组成了后期剪辑小分队,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
凹凸镜DOC:我设想一下,其实是在重新审视自己,往下挖内心的那个过程最难。
李新月:确实,我回到哈尔滨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找工作了,可以想见的又回到了北漂的状态。我感觉,如果我再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,这个片子很可能就会中途放弃。一直坚持做这个片子是最难的。需要让自己在一个“悬崖边上”的状态里。
凹凸镜DOC:“私人记忆+时代背景”融合成了本片最大的特点,你认为“私影像”的魅力和意义是什么?
李新月:现在任何人拿起手机都可以拍摄,但我认为以私人的一个视角,有思考在里面,可以抵达更多人的那种创作,不只是私人的私密的。
比如说像“母亲影展”里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妈妈作者叫“五花肉”,她就是拍自己在云南的生活。一个人独居,房屋改造,儿子给她送的礼物是内衣,还有她一个人在黑暗中洗澡,边洗澡边参加工作坊……可以说是很私人的,但是又能够抵达很多人。

新月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返场谈
凹凸镜DOC:这部纪录片诞生于草场地“民间记忆计划”工作坊,请讲一下参与这个计划的全过程,以及对你的创作有哪些帮助?
李新月:2020年的时候,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,正好是疫情,草场地的工作坊转到了线上,只要你对写作或者影像感兴趣,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创作或者想法来分享。吴文光老师作为主持人会分享一些草场地作者的创作案例,现场也会有一些即兴的素材分享和身体出场。
大家发现线上的空间比线下要大很多,因为参加者来自五湖四海,各种时差都能在线上聚在一起。每周固定会有读书会、创作工作坊,以及不定时的个人剪辑推进工作坊,都是作者们自发组织的,随时有新的人会加进来。
我还做过一个统计,我做这个片子的三年多时间里,和草场地的伙伴们有过大概39次的剪辑讨论。我们一起去阅读拍好的素材,大家再交流想法。这个过程改变是巨大的,因为以自己的视角去看自己的经历,容易深陷其中,但是通过别人的反馈能够发现,个人的事情挖深以后,和别人就是连通的。
凹凸镜DOC:片子里有一个镜头印象很深,大家在线上集体摘口罩,这个也是工作坊的一部分实践吗?
李新月:这个是梦奇发起的,因为她之前都是做线下剧场,但当时是线上,所以就招募了大概20个伙伴一起,做了一个叫“阅读病毒”的线上剧场。那个口罩就是表演的一部分。
身体也是一种实验,就比如我的片子中投影的那部分,也是一个身体尝试,但还没有线下那般放松打开。现在线上就在尝试各种身体,如果你周六来正在进行的草场地“身体/写作/影像工作坊”的话,你就会感受到线上身体现在也是可以相当的强烈,就能感受到那种线下的感觉。

《新月一章》里使用的“桌面电影”的方式
凹凸镜DOC:无论是参与工作营做志愿者,还是工作坊的创作,你是会在一个集体或者组织中找到价值的吗?
李新月:对,会需要社群的存在。因为好像一个人在这种社会潮流里,很难去抵抗,很容易就被淹没掉,但是在这样一个社群里面会有更多支持,一群人能更好地往前走。
凹凸镜DOC:完成这部片子后,对你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么?
李新月:我的人生轨道发生了转向。本来我是可能回到哈尔滨找工作,但现在我是在吉林省的一个乡村,那是我姥爷老家,他离开这个村子50多年了,但我试着在这里生活下去,继续创作。一个是拍摄,一个是种地,我种了一亩稻地。
教资已经考上了,但不准备去做这方面的工作。
我之前在工作坊里也讨论过《新月二章》的大纲,想从我现在生活在这个村里子,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开始叙述,也会有和姥姥姥爷相关的记忆在片子里。

新月在幼儿园时留下的影像
凹凸镜DOC:平时有什么爱好?可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/一首歌/一本书吗?
李新月:我的生活其实很单调的,没有什么爱好。我想到的书是我看过最长的一本小说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。讲两个女性很复杂的那种关系,也有女性书写里面的那种“痛感”,这个是共通的。我记得最后女主角埃莱娜对自己的总结——我的一生,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,是有痛感,但也很有力量的。
凹凸镜DOC:“私影像”会成为一种风气吗?今年FIRST入围的很多都是讲亲密关系,你感觉你的片子独特性在哪里?
李心月:以前的纪录片,导演会去拍公共议题,像是记者深度调查那样去拍摄,有一种公共责任在里面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,现在更多年轻的作者在拍自己的家庭,自己的生活困惑,确实是变多了,但如果说要走向更开阔的一个视角,还是要再做努力。
凹凸镜DOC:听你这么讲 ,是不是任何的记录其实都是有意义的,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“决定性瞬间”,哪怕是最无无聊的日常,你们都觉得是有意义的吗?
李新月:对,任何任何素材都可能是很棒的,就看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和编排。但我觉得我确实需要学一下手动挡,拍摄时能把曝光调好。

影片介绍:2020年7月,我回到离开六年的老家哈尔滨,人生的轨道在24岁刹车,我开始在顺流而下的生活里重新审视自己如何被塑造。“新月”是母亲给我起的名字,来自于她在疼痛和混乱中仰望的美好,引领我回望我所出生的九十年代,检视美好仰望与残酷现实间永恒的缠绕。

关于导演:
李新月,1996年生于哈尔滨,大学毕业后北漂两年,2020年返回哈尔滨,参与草场地工作站创作社群,开始以“新月”为名的系列写作和影像创作。


凹凸镜DOC
ID:pjw-documentary
微博|豆瓣|知乎:@凹凸镜DOC
推广|合作|转载 加微信☞zhanglaodong
投稿| aotujingdoc@163.com
放映|影迷群 加微信☞aotujingdoc
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
金勺子配资-金勺子配资官网-线下配资官网-实盘配资平台有哪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实盘配资平台通过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议程动议
- 下一篇:没有了